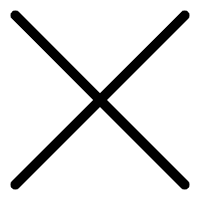对话易介中:VUCA时代中国人的理想生活 / UED&界面城市观察专栏
专栏案: 由《城市 环境 设计》(UED)杂志、界面楼市、界面城市频道联合策划的UED&界面城市观察专栏,邀请专家、学者、设计师、企业代表等嘉宾,围绕多个和中国人的城市、住居、传统有关的主题,以案例、专访、对话、文章的形式,展现群星璀璨般的内容。 "一千个读者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正如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理想中的生活方式,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生活场景。随着社会的高速发展,当代人的生活方式发生结构性变化。这种变化,不仅是年龄、地域、文化程度和收入这些物 理性差异造成的,更是生活方式及意识形态等价值观差异带来的。每个人都在朝着自己的理想世界曲折前行。 2022年8月,首届【新国潮大会】将举办,将集结顶级专家学者、国潮品牌主理人、主流媒体人共同探讨国潮品牌增长力,助力中国经济双循环。 本期专栏,UED&界面城市独家对话易介中博士,围绕“城市”、“韧性”、“居住”、“城市建筑”、“传统和符号”、“普利兹克建筑奖”、“在地性”等诸多主题,共同探讨当代生活方式变迁对中国的建筑和住居文化的影响和意义。 (点击下图了解预告详情)
易介中 博士
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文化和旅游工作委员会会长,大有智库城市更新专家委员会 常务副主任兼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文化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中央美术学院城市设计与创新研究院副院长,《城市 环境 设计》编委会专家委员。
-
以下为对话实录
-
City and Resilience
关于城市和韧性
孙宁卿:
您现在在上海,此刻对城市韧性(Resilient)有什么切身的感受?
易介中:
韧性城市(Resilient City)是最近很流行的一个词,2020年通过的十四“五”规划和二零三五远景目标里首次提出建设“韧性城市”。我觉得韧性这个词还不错,中文里这个字的意涵很丰富。狭义的韧性城市就是说,当一座城市遇到特殊时期,能不能保证迅速拥有适应能力?广义的韧性城市,我会把“城市更新”都纳入研究范畴,因为我认为由于错误决策而造成城市与建筑对未来发展的不适应性更是一种“综合性灾难”。接下来这种VUCA错综复杂的时代,世界大势唯一的“不变”就是“变”。
比如我爱人平时让我买东西时,她要我买1个罐头,我就会买1打罐头。最近她就忽然感到说,幸好我平常有囤货的坏习惯。其实我本来是个坏习惯对不对?尤其是买了一大堆成药囤着,这次我还用库存止痛药帮助邻居呢,本来买东西就应该是“够用”就好,由于我的潜意识焦虑以及没安全感造成总是买超了。
孙宁卿:
有很多备份,这就是一种韧性。
易介中:
对的,超级韧性!所以我们小区邻里之间自然而然在疫情期间形成了“库存应急共享群”。刚好这段时间大家也好好去去库存,准备迎接下一次特殊时期。远亲不如近邻,在这种特殊时期,就算住在隔壁小区的近亲也常常不如近邻啊。

▲VUCA都包含什么?©界面楼市
孙宁卿:
您觉得中国的城市有哪些独特之处?
易介中:
我觉得我们在中国谈城市发展问题,我们首先应该先谈谈“小区”(城市住宅小区:neighbourhood、居民小区一般简称做小区,是指以住宅为主并配套有相应公用设施及非住宅房屋的居住区、花园住宅、住宅组团),对于全球城市住宅区而言,大陆大部分的小区几乎都不小。带着一圈围墙的小区是一种很独特的城市单元,我记忆中去过的所有城市像大陆这样的,我台北的家在忠孝东路边上,忠孝东路走九遍,几乎每一遍都可以经过我家门口。
中国目前超大型小区排名前九名的人口累计接近200万人,差不多是一个地级市的人口等级。换句话说,这些小区的社区主任所管辖的人口,估计一般的县长都赶不上。
单一小区的综合极致化表现应该是贵阳花果园项目吧,它是全国最大的棚户区改造项目,位于贵阳市中心。项目居民超过43万,总规划面积10平方公里,总拆迁户数20000余户,涉及拆迁人口10多万人,拆迁面积400余万平方米。项目总投资1000亿元,总建筑面积1830万平方米,是集住宅、商业、艺术文化、商务办公、旅游、智能生活服务为一体的大型城市综合体。
全世界应该绝大部分的城市由于土地私有化的原因,太难实现如此规模宏大的封闭式管理社区。当然在特殊时期如果要封控,实施起来也太困难了,全球城市大部分的人,应该出家门就是马路或巷道,除了规劝以外,难道能把他们家低层住宅或公寓楼铁门电焊封死?
查资料,在中国的大部分地区,封闭式小区的建设高峰有两个,一个是上世纪50年代兴起的单位大院,城市里各个独立的单位圈一块地,建一个集办公生产、居住、后勤以及各项生活服务于一体的大院子,作为福利提供给职工,外人不能随便进出,单位大院仍然是国内许多城市的基本构成之一。有数据统计,光北京就仍现存3700多座单位大院。
另一个高峰期是1998年之后。当年我国进行了住房制度改革,取消福利分房,实现居民住宅货币化、私有化。一时间,房地产大热。建筑形式、景观设计、物业管理、社区营造、生活理念等许多方面都成为开发商努力追求的“卖点”:顾客喜欢安全和私密的环境,那就实行封闭式管理,少设置出口,周边围墙盖起来;中国人喜欢居住的依山傍水,那就在小区内部精心打造宜人的景观。这样一来,封闭式小区成了我国小区开发的主流形式,且越是高端住宅区,封闭性有越强的趋势。
这种空间结构在各种特殊时期的管理优势不言自明。

▲平遥古城(左)和天通苑地区(右)尺度对比 ©UED
孙宁卿:
这种喜欢“围起来”的空间结构能产生什么不一样的事情?
易介中:
首先,围墙内更容易形成居民安全感、归属感与人情味的小社会,这点比马路边的住宅有着更大的优势,尤其在错综复杂的世界变化快与碳中和目标的各种背景下,我们的小区如果大到能够容纳数万人的话,围墙内许多自给自足的内循环模式就会很有时代优势。譬如都市垂直农场,科技猛进的今天,几亩地100米以内高度的一个垂直农场与垂直太阳能蓄能场,够平均5万人一年绿叶蔬菜的的基本保障供应已经不难了,未来小区的投资预算是不是应该考虑这样的有意义的设施,而不光是景观造景与破坏地球的建材堆积?“可食用景观Edible Landscape”在未来也将必然成为人居的标配,同时助力加速城镇化以及大量减少物流的人力物力能源消耗等,甚至是一个巨大的社区氧吧。
如果我们针对中国人这种骨子里就有的田园梦想生活方式,把它放大一点来看,功能再完善一些的话,它就是极致的碳中和可持续发展理念。
孙宁卿:
形成一个完整的生态圈,对不对?
易介中:
是,我更偏向定义为一个“中国人居文化文明生态圈”,一切都要感谢互联网,造就了有围墙的理想小区,跟钱钟书“围城”刚好相反,外面人不想也不用进去,里面的人不想也不用出来,想想挺元宇宙思维的。
所以,理想小区规划的好,就可以同时满足对外为辅与对内为主的文化健康体育医疗日照中心、SOHO、联合办公、社区商业及农场及各种共享经济等。
同时我们应该大声疾呼去重新正视与拥抱SOHO时代,可惜目前的SOHO中国只是沦为“案名”而不是给斜杠人生提供最重要的的工作生活游憩方式。这次的疫情至少教育了世界,某些行业居家办公绝对是可行的、天经地义的、高效的,甚至我都开始思考我从事的创意咨询等行业要办公室的目的除了培养新人必须手把手教以外还要干嘛?有什么了不起的伟大思想不能在微信上留言说明白?尤其在德国、加拿大、西班牙、冰岛开始实施周休三日的趋势下,居家新经济应该是需要认真研究了,当然居家办公最大的受益者还是资深的智力工作者,尤其是我们这种本身就宅的不亦乐乎又喜欢邀请老友在家里侃大山的族群。
何况我们从19年到现在,不习惯也得习惯居家办公,从习惯到热爱也就是一步之遥。
▲垂直农场满足人类食物需求 让农业生产走进都市
©高工LED新闻 (gg-led.com)
孙宁卿:
未来的生活方式其实也挺传统的,古代士人的园林就是soho,住在里面,也在里面工作、打理事务。
易介中:
拙政园本身就是一个再豪华不过的超级SOHO思维。虽然没有太多的研究,应该屋主足不出户很长时间问题不大。
经过这次的疫情警醒了社会紧急救治的重要性,社区需要的常规配置反而是有专业医疗人员的第一时间紧急救护、配备AED心脏急救设备、库存保障食品等,平常大家最不关注的马斯洛心理需求金字塔最底层的“基本生理需求”中食物、健康、活着反而是最最重要的。小区里的种再贵的名贵树种也没有救人一命重要,似乎一个小区越大越有适应未知的“韧性”能力,似乎“韧性”、“人性”、“任性”都跟小区规模有关。
孙宁卿:
看来很多城市与建筑的生态圈都需要重新思考。
易介中:
中国特色的城市与建筑生态圈就是变化很快,有些制度在全球化事业里现在反而看出了优势,譬如中国的设计院制度就是一个很独特的机构,很多时候老是要面对社会及业内要求改革的压力,各个专业齐全的时候,很容易给大家都不突出的印象,也就是我们说的短板效应,很容易因为某个专业短板把其他专业一起拉下水平。可是这几十年的造城运动,如果按照所谓先进的专业分工模式,估计现在还有90%的房子还在各专业之间扯皮呢。
不去跟慢工出细活的欧美日国家相比,如果跟发展中国家相比,我们的设计院简直是神一般的存在,有多少国家的各种专业层次不齐,建筑师要牵头整合所有专业是多大的工作量与各种沮丧集于一身的压力,在中国可是隔壁办公室的同事啊。中国在亚非拉等第三世界国家投资与工程总承包等业务,我相信中国特色设计院一定是海外发展非常重要的核心竞争力。
▲1909 Theorem(此处理解为“原型”比较好,编者案)
©雷姆·库哈斯《癫狂的纽约》
Dwelling and Living
关于居住和生活
谭潇:
什么样的居住模式比较好?
易介中:
三居室、两居室还是一居室还是一个床铺位,跟有多少钱是有关的,朝向东西南北、有没有景观、高层、低层还是地下室,跟多少钱也是有关。假如一个大学毕业生可以用30万青年住房零利率贷款买一个住在上海静安嘉里中心地下3层的“有着人造太阳光与恒温恒湿增氧新风零污染的15平米无印良品青年公寓”,然后上班就是直接坐电梯到楼上充满阳光的办公室,中午居然还可以下楼回家睡午觉,等到挣了钱再考虑下一个酷窝...
我的结论就是“城市的本质上是人类的交易中心和聚集中心。在城市核心区只要安全、方便,工作努力的上班族买得起的就好。”。无论住在地下室还是纯朝北,需要阳光的去公园、屋顶晒太阳,而且现在专业日光浴设备非常普遍而且科学证明对人类健康帮助比直接晒太阳好多了,规划师与建筑师们是不是应该无时无刻要努力不懈的一直要试着找到住者有其屋的各种解决方案啊?哪怕不成熟,也是要努力啊 ,这不就是如同医生必须救死扶伤不允许见死不救的天职吗?
我一直不理解一个简单的加减乘除而已的问题为什么解决不了,钱少买电动自行车,钱多买汽车,骚包的去买劳斯莱斯,至少都是车,我们的每一块土地都是国家的,难道不能打造容积率20的小区给刚毕业为了美好未来而打拼的青年人吗?现在的年轻人本来就趴在手机上电脑前,小区里设计出一个可以吃喝玩乐的社交型小公园不就解决了阳光与遛狗的问题了吗?每天晚上都有脱口秀、音乐会、BBQ,年纪大了挣钱多了再换一个容积率10的就好了啊。有那么难吗?在这个充满欢声笑语的社会里,平均只要步行10分钟以内就能到工作场所、商业空间、戏剧院、美术馆、医院等,对了,其实很多人都是SOHO,那个时候所谓的中等收入阶层就是有一台尽量环保节能的小车而且郊外有一套小别墅。
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是不是通过“保证房地产土地成本降低最大化而且能容纳最多居民的容积率”能解决一部分呢?如果调研大部分经济发达区域城市居民生活痛苦指数,买房难、看病难、读书难如果是排前面的,怪房间阳光不好与怪层高不够高这种痛苦指数能排到多少呢?
更不要忘记了,我们现在是一个互联网WEB 3.0的元宇宙时代,城市规划者不能再用前一个世代的思维来思考下一个Z世代的需求。国际上已经有大量共享经济思维的社区,连厨房功能都弱化到只是一个简单的加热食物的台子,洗衣机也只剩下迷你型洗贴身衣物的,所谓“家”的功能最后就是睡觉的地方,社区内更重视的反而是宠物优先的权利。

▲从花园式的低密度郊区远眺高密度市中心
©Andrew Merry / Getty Images

▲电影中的太空田园城市 ©《极乐世界》
孙宁卿:
如果说刚才谈的这些是“应当怎样”,那么现在在增量变存量、高密度发展的当下,我们的居住方式正在呈现怎样的改变或趋势?
易介中:
现在社会面临着两大机遇,一个是人口老龄化加速,而且由于疫情长期居家购物、刷视频与健康码的“必须化”使得银发族智能手机应用普及率达到了新高;随着老龄化社会的来临,必然会出现人们生活居住方式的改变,空间和服务的“适老化或全龄化”是我们必须要正视的问题与新机遇。
正如我们现在正在做的城市更新(有机更新/微更新),许多是针对社区养老新生态圈的概念去实施和探索的。而另一个重要方向是特色生活方式与日常生活方式的创新融合,比如在疫情后,人们的未来生活工作方式将会发生不可逆的加速巨变,尤其是居家办公、外卖配送、团购等成为人们新的生活标配,更不用说未来的元宇宙与智慧社区等众多创新应用场景,显而易见的是,家庭里的建筑设计、空间关系、家具设计、网络功能等都要做出相应的创新,阳台要可以停无人机接送货,传统厨房功能则会被渐渐弱化,每家每户都配备微型水培蔬菜机器,等等。
所有的变化都会形成未来生活方式新产业,从而产生新兴的赛道、行业和风口。

▲典型的智能家居、家电系统

▲家用智能蔬菜种植机
孙宁卿:
有人说,当前的变局下,人们又回归了家庭,厨房可能反而会出现一个回归。但是单身的和老年人不一样,年轻人很多都不做饭了。可能不同的年龄段的居住方式的有一个不同的变化趋势。
易介中:
大家务必要清楚,老人的生命质量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于饮食健康,老人自身很难做到三餐正常的吃到营养均衡的新鲜饭菜,同时老人使用厨房的危险性也会逐年增加,另一方面年轻人吃外食的机会太大,厨房的使用率也是越来越少。
最近中国有一个大风口就是预制菜,就是非常符合社会的发展趋势,它在全球范围非常发达,尤其在日本已经做到了极致,日本中高端消费人口众多而且市场成熟,是很多创新型消费领域的最佳试验田。先不谈预制菜好不好吃,至少比你自己去市场买的菜可能食品安全问题更容易解决,因为能从源头解决起,同时由于工业科学化标准化高,所以厨余量锐减。必然是中国人餐桌上的重要趋势与选项。
Architecture of City
关于城市建筑
谭潇:
现在城市的建筑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比如聚焦新的领域:生态环境、历史价值、文化导向、产业升级、智慧生活等。这种新时代的背景下,中国城市建筑有哪些时代特点?
易介中:
回到这个挥之不去的错综复杂世界,城市建筑本来应该具有高度可持续、弹性、韧性、随时可以调整功能的空间形态,很可惜我们城市的决策者与设计师普遍充满着“普信思想”。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
当一个建筑从开始设计到最后完工的时间差,我觉得有大概率是完工就开始落后,这还是指全球领先思想的建筑师做的设计了,新技术、新思维、新业态层出不穷,如5G、物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数字人民币等新技术将会迅速的不停的改变人类的生活方式、社交方式等。所以盖好了就是一个坚固不可动摇的大家伙——建筑——必须要拥有适应性、可以随时改造以适应未来生活的空间。
现在中国有多少“普信”商场,刚封顶就落后几条街了,有多少“普信”写字楼及产业园刚打完地基就经济与产业转型了,所以设计师应该行行好就做酷的不行不行的尽量高空间尽量无柱子的大盒子,做个可以随时因为产业逻辑调整而简单轻装修重装饰改造的弹性空间。
说到底,底层逻辑就是不要折腾地球,要低碳环保,我们有幸活在一个极致追求碳中和的大环保时代,高能耗、高材料耗费、老是拆拆改改的建筑物和没有灵活适应性的空间结构,不可回收、过度包装、远距离物流等都是要被淘汰的。如果你的设计思想能把碳中和理解透彻,那么一切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了。

▲法国巴黎的一座采用高适应性设计理念的学校建筑
©Muoto architects
孙宁卿:
嗯,其实地球不怕折腾,主要是折腾地球就是折腾人类自己。我这是拾丁仲礼院士牙慧(笑)。
易介中:
是的,别忘了地球已经有5次生物大灭绝,人类也不过是下一次灭绝前意外崛起的生物。
说到人类爱折腾,这次由于种种情况而出现了“团长”这个社会新角色,也多亏我们小区的众多团长,他们的热心公益勤劳正义勇敢才能让我们平安度过这些时日。我平常的性格是必须要做游戏规则主要制定者,但这段时间也是非常安静的闭嘴配合各位团长的(笑)。
TCArchiteture and Symbol
关于传统建筑和符号
谭潇:
中国传统建筑似乎也是具有高度的适应性。作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对现在中国的建筑设计影响多吗?
易介中:
中国古建筑本身就具有很高的适应性和绿色低碳思想,它基本采用框架结构,墙和门都灵活可变,各种构筑件也是互联相通,非常利于更新改造。从皇宫大殿、庙宇再到民居基本都是采用同样的结构逻辑,以不变应万变。这也正是现在“碳中和”可持续生态发展思维的极致表现。传统建筑和现代思维科学的重叠了,我现在的其中一个事业就是创新型复原巨量的古建拆迁保留的古建构件,比传统的钢筋混凝土、钢结构的建筑有意思多了。
不过我也提出一个灵魂质问:在一个欧洲古典巴洛克教堂式的空间里面开茶馆,或是在一个中国庙宇式传统木结构古建里面开咖啡馆,你们想一想哪一个更能感受到中华文化?
再加码,如果是茶馆里还听相声,与咖啡馆里还听脱口秀呢?
谭潇:
那在很多现代建筑,尤其是一些住宅项目的设计中,有很多借鉴中国传统建筑文化元素的内容,比如,檐角、礼序等,您觉得这些传统文化元素在现代城市生活美学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又起着哪些作用?
易介中:
身为中国人,全身上下里里外外骨子里都是“中华符号”。我的易姓就是变色龙象形文字演变过来的,所以我骨子里一直不变的就是“变”。中国就是符号大国,中华文化就是我们无论穿西装用手机喝咖啡都不会丝毫改变的“文化基因”,尤其是各种符号包围了我们,不管你喜不喜欢,再前卫的国际建筑师做了国家体育馆也得“被符号”为“鸟巢”,再怎么前卫的建筑也离不开“山水”“太湖石”等中华民族习惯的符号,我就不相信中国有一个前卫建筑师跟决策者汇报方案说我做的就是一个“居住机器的方盒子”,那是柯布西耶才有的特权。
既然绕来绕去都离不开符号化,也就没有所谓这个符号比那个符号高级的说法吧,符号无论是后现代堆积、故事线、创意来源、设计理念都可以,只要是相同用途、相同业主、相同造价、相同时间等相同条件,谁能做出更高明的设计谁才是值得被尊敬的。譬如题目就是大唐主题风格收门票的5A景区,消费者就是旅行团为主,难道不做出一堆“老百姓心目中的仿古建符号”,改为做出一堆现代形态的“建筑师意向唐风”,除了建筑师的铁杆粉丝以外会有人买门票进去看吗?如果在秦皇岛海边的阿那亚不做出讨好特定小众社群的“前沿接头符号”建筑群与生活方式能行吗?

▲洪崖洞区域景观 @图虫创意
Pritzker Prize
关于普利兹克建筑奖
孙宁卿:
您怎么看王澍先生的作品?
易介中:
在我对建筑的认识里面,第一个层次是对与错,第二跟层次是好与坏,第三个层次是成功与失败。我今天说了半天就是在谈第一个层次吧,因为我认为很多情况是错的。
谁能举出普利兹克历史上有哪一个得奖建筑师后来被证明是颁错奖了呢?总不会刚好是王澍吧。
对于我这个大学与硕士都是建筑学院学建筑设计,而且那么多年从事相关行业的人而言,我本人不是普利兹克建筑奖的粉丝,因为我认为有更伟大的在世建筑师并没有得到。
但是我确信只要得过普利兹克奖的人至少都有不少作品是“对的”,而且他们一定至少有一个作品是“好的”,至于说是不是“成功的”得留给后世来评价。
每年约有五百多名从事建筑设计工作的建筑师被提名,由来自世界各地的知名建筑师及学者组成评审团评出一个个人或组合,以表彰其在建筑设计创作中所表现出的才智、洞察力和献身精神,以及其通过建筑艺术为人类及人工环境方面所作出的杰出贡献。
2012年2月27日王澍获得了普利兹克建筑奖,成为获得该奖项的第一个中国人。大家可以帮忙调研一下,如果不出意外,他应该是唯一一个没有建筑师执照的得奖人,这真是一个非比寻常的VUCA时代。
王澍得奖时说:
“作为一个年轻的建筑师,我必须说,要感谢这个非比寻常的时代,正是这个时代的中国巨大的发展和史无前例的开放,才可能让我这样一个建筑师,在如此短的时间里有这么多的机会去进行艰难的建筑实验。”
评审委员会主席帕伦博颁奖说:
“王澍之所以能够得奖,是因为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建筑领域最具竞争力的市场和建筑发展的实验场。基于良性和积极的市场需求,这种竞争正在催生一种全新的中国建筑风格,它既尊重传统和地方特点,又能满足当下的紧迫需求。”
我去过杭州中国美院的象山校区,我第一个反应就是羡慕嫉妒恨,同时愤怒为什么大部分的美术与设计学院教学空间还都是丑陋不堪呢?很多人说象山校区有些空间不好用不合理,我觉得设计教育目前是在救命的阶段,救命的特效药有副作用合情合理。我绝对合理的认为,自从象山校区以后,我看到开始重视校园规划建筑设计的艺术设计学院,甚至从幼儿园、小学到高中都有精彩作品。
再来,我要向他致敬的是,他居然做到了对于得奖建筑师来说最难的事情,就是没有开始大肆抢活到处敛财——尤其是中国市场,正常的中国第一位普利兹克奖得主,不搞几个甲级院全国连锁、员工低于千人,都是太客气了,多少普利兹克建筑大师的最大型的失败作品都是留给了中国。
就凭这点我必须正式的向王澍致敬,虽然我们彼此不认识。
同时可以观察从王澍开始,普利兹克开始更加重视文化多样性、爱地球以及政治正确了。首先是开始重视发展中国家以及第三世界国家;第二是开始重视社会责任、性别、环保、节能、脱贫等符合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议题。
孙宁卿:
比如社会关怀或再生材料之类的。
易介中:
我一直认为谢英俊应该得普利兹克奖的。我希望有机会我们策划一个专题好好跟他讨论他创造的智慧钢构系统。
▲点击了解UED文章:[谢英俊]从木到钢的技术美学 | 王蔚对话谢英俊
Locality and Chinese Dwelling
关于在地性
和中国人的房子
孙宁卿:
回到在地性的事情上,能谈谈国潮吗?
谭潇:
比如近年来,国潮兴起,文化复兴成了一种势头。无论是国潮文创,还是汉服和礼制在年轻人中的复兴,这些国潮文化都给当代年轻人带来了一种和以往不同的追寻目标。
易介中:
你提问里的“国潮”严格意义来说应该是指“大国潮风”之下的一个分支,即中华传统文化创意,中国Z世代骨子里真的就喜欢中华文化,他们被称为“互联网原住民”,所有接触的信息无论乡村还是城市都是全球化思维的。在这种信息发达的环境里,他们很容易感受到身在一个伟大强大的好时代,北京奥运、上海世博会、高铁、航天事业等民族自豪感自然而然形成文化自信。所以说国潮复兴从一定程度上是通过创新科技新媒体传播赋能中华传统文化的。
谭潇:
那新中式呢?新中式审美的住居文化就像是繁华都市中的诗意栖居。在您的理解中,现代新中式住宅有标准吗?应该有哪些元素?
易介中:
新中式的概念其实我们已经谈了快20年了。它是现代主义建筑到后现代的一个文化自信生活方式,只是很久以前新中式是为了第一批先富起来的高质量人群打造的,现在应该是面对所有客户群体的基本发展模式了。新中式概念首先离不开当代中国人感觉舒服的生活场景,这个是随着城市、人群状况而随时需要调整的,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希望建筑师们多研究思考高密度高层建筑条件下的新中式住宅愿景,这才是有价值的探索,尤其是室内设计、生活物件及家具设计师们,这是你们最好的时代,大家好好思考这个离不开手机、电脑、回家葛优瘫的新中式生活方式吧。

▲当代文创 @图虫创意
谭潇:
每期都要问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这个栏目,有一个想尝试探索的主题:“当代中国人理想中的房子”。您觉得当代中国人理想中的房子应该具有哪些要素或者标准?
易介中:
这个问题我永远放在第一的是,“中国人人人有房子的理想”如何满足?接下来我希望能从小区、景观、建筑、室内、家具、生活物件、气氛装置、艺术、植栽等当代中国人喜欢的生活场景来一一探索。
我会站在策划师、规划师、建筑师的角度,希望打造轻易能适应未来生活多变的弹性空间与共享生活体系,建设高层高密度不再“何不食肉糜”的荒谬逻辑“宜居标准”,打造符合未来大量城市新增人口需要面对的人多地少特色的宜居标准,尤其是打造让人们负担的起、住得起的房子,这就是我认为“当代中国人理想中的房子”。
-
全文完
-
-
采访人
-
孙宁卿
建筑师/编辑
UED媒体负责人
谭潇
编辑/记者
界面楼市资深记者
撰文&编辑 | UED&界面城市观察